
近日Patagonia创始人Yvon Chouinard宣布将公司的所有权捐出,用于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事业。目前Patagonia公司市值30亿美元,公司98%的股份将分给非盈利组织Holdfast Collective,其余2%和表决权则分给「Patagonia目标信托(Purpose Trust)」。Chouinard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最大程度地保持品牌目标,即「保护地球家园」,同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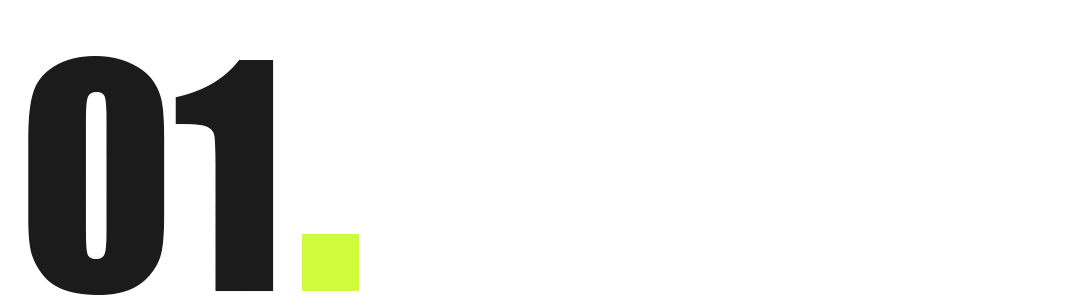
今年83岁的Chouinard「起家」于位于美国加州的父母家后院,最初的事业是为攀岩者手工制作岩钉。半个小时制作一个岩钉,一个卖1.5美元,收入足够他白天攀岩、傍晚冲浪和自由潜水,并游荡在优胜美地和落基山脉之间,用5美分的猫粮罐头和土豆填饱肚子。24岁时他被捕入狱18天,罪名是「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,没有明显的生活来源」。30岁出头的时候,Chouinard开始进口和加工用于攀岩的厚实外套。几年后他和朋友Doug Tompkins来到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攀登菲兹洛伊峰(Mt.Fitz Roy),之后将公司改名为Patagonia,logo正是菲兹洛伊峰的剪影。而这位同行的朋友正是The North Face的创始人。企业家和抱树者(tree hugger,即环境保护狂)的双重身份在Chouinard身上交织,早就了许多称得上古怪但又仿佛说得通的行为:比如2011年的黑色星期五购物节,他在纽约时报上刊载大幅海报劝诫消费者「别买这个夹克」;比如作为公司老板,他鼓励员工在冲浪季来临时减少工作时间;比如他名列福布斯亿万富翁榜,却把自己称为「土包子(Dirtbag)」,且据说基本不使用手机和电子邮件。有这些作为背景,Chouinard捐出公司利润的声明算不上难以理解。事实上,Patagonia很早就开始了对环境保护事业的捐赠:最早是将利润的10%捐赠给基层环境组织,后来将这个数字提升至销售额的1%。Chouinard在最近的声明中表示「地球是Patagonia唯一的股东」——从起家的本金、到建立公司的灵感、到购买产品的群体和支撑公司运行的员工,Patagonia无不与自然深度绑定。有了自然,人才去户外,才需要户外用品。如果自然不复存在,一个户外用品公司就失去了意义。Patagonia不是不经营了,但他选择在经营企业的同时,也经营自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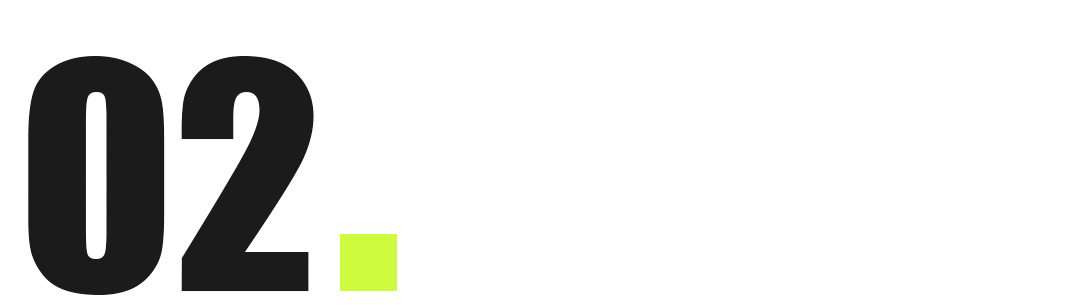
不过当今的都市打工人怕是很难与Chouinard共情。在狗屎工作和消费主义之间被反复规训的打工人,实在不必背负关心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道德负担。事实上,很多人对自然是陌生的——餐饭来自外卖,百货来自电商,风景来自屏幕,冷气来自空调,所有消费品都是现成的。如果你生活在大城市,那么可能一天到头「接触自然」的机会仅有从家门到地铁、从地铁到公司那一段的环境暴露,吹一吹城市热岛的高楼风。我朋友的小孩四岁,小朋友认为只要想吃零食水果,就可以「找快递叔叔」。虽然在旅行选项所剩无几的今天,比起动辄上千的京郊民俗,在山野中行走是最经济的出游方式之一,但往返至少一天的时间成本对绝大多数都市人是一种奢侈,常年办公室久坐或者应酬也让很多人失去对心肺臀腿功能的信心。如果生活体验和身体感受与自然环境脱节,那「保护自然」很容易沦为口号式的空谈,甚至成为以更多的消费刺激快感的借口。2022年,国内露营经济继续逆势上扬,有数据显示规模可达千亿。但在千亿级消费的背后,必然是庞大的闲置与重复购置、资源消耗、一次性用品使用,和留在营地里没有带走的大量生活垃圾。虽然这些都不出现在精致的九图plog中。以「出片」为目的的旅行和「搬家式露营」有其耐人寻味之处——一方面,急速增长的关键词搜索量和户外用品销量反映出人对自然的向往。在生活的多重压力下,自然始终可以唤醒人的活力。但它的另一面亦是对自然的消费和消解。程式化的商品清单意味着对自然的体验都要按照剧本进行,即便自然是多样亦多变的。在电商和滤镜的加持下,每个人都看起来像是资深户外玩家——如果社交网络的图片展示是一切体验的出口,那么是否真的深度户外又有什么关系呢?

一边是山林、海洋和雪原,一边是产品、货架和广告。如果处在这两者之间的打工人注定只能做一个消费者,那么我们究竟在消费什么?换句话说,在消费的层面上,我们如何看待山林?山林是我们逃脱无处不在的商品消费的避难所,还是另一个新奇的消费场景、另一个把已买过的东西再买一次的理由、另一片值得夺旗和拼杀的商业蓝海?又或者,山林与消费不必全然对立——如果我们进行一种目标导向的、深思熟虑的消费,那么商品不仅可以让我们开启一种全新的活动,也可以帮我们深度体验所处的世界和当下,获得真实的身体和心灵感受,并激发更多回馈山林、分享价值的行为。这种可能性过于理想吗?或许是的。毕竟连Chouinard都说,Patagonia试图建立负责任的商业模式已经50年,但也才刚刚开始。但这种可能性也取决于一个简明的选择:生产(或者消费)是否服务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目标?这正是Chouinard的选择的可贵之处,即用实际的捐赠行动证明,比起增长和盈利,Patagonia选择投入尽量多的资源,服务企业自2018年确定的目标:经营拯救地球家园的事业(in business to save our home planet)」。为了最大程度地保全这个目标,Chouinard和公司的管理层没有选择卖掉公司然后捐出所有的钱,也没有选择让公司上市(「在上市的压力下,一个企业会转向创造短期收益、牺牲长期责任。」)他在9月15日发布的声明中说:「我们希望能够兼顾做正确的事和挣足以覆盖成本的钱,这样就可以影响顾客和其他企业,甚至改变整个系统。……我们没有选择上市(going public),而是选择目标(going purpose)。我们不能从自然中攫取资源以换取财富。我们选择利用Patagonia的收益去保护所有财富的源泉(即自然)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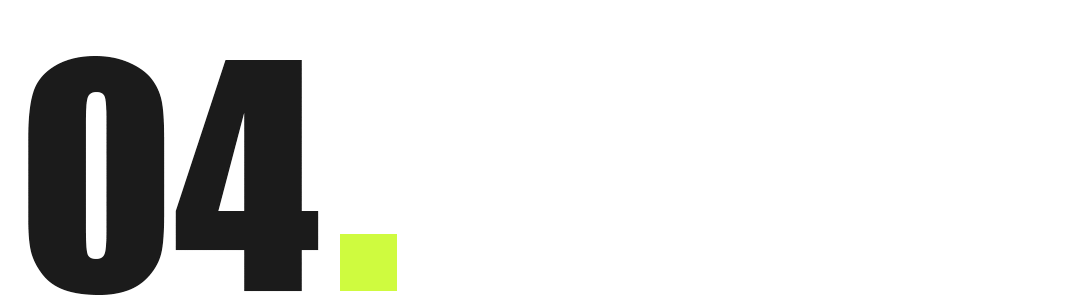
人能「保护自然」吗?我认为无论是政治领袖、商业巨子,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,想以自身力量保护自然都很难。我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:自然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,足够消化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。但是,由于可消费的商品日益丰富、消费场景不断延伸、原材料来源越来越广泛,毫无疑问,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无论从强度还是范围上都今非昔比。况且我们确实更加依赖那些自然无法消化、也无法再生的产品和资源:塑料、玻璃、电池、石油、煤炭。那些我们熟知的、甚至熟视无睹的品牌、企业、产品,确实正在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另一方面,随着环境承载负荷越来越大,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态系统服务(ecosystem service)也将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,例如:污水排放、垃圾填埋、气候调节、基因资源、生物安全、昆虫授粉……当然还有休憩娱乐。当资源供给足够丰富时,这些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;但如果资源枯竭、排他,那么成本的增加必然层层传导,反映在我们的账单上。所以消费可以有两个面向:一是为资源的成本付费,二是为资源的保育付费。二者并不矛盾,但如果只选择前者,那么我们只能随着资源越来越少、成本越来越高而支付更高的价格、获得更有限的服务。如果兼顾后者,我们就有希望永续利用资源、更长久地享受自然的丰裕和美,并且从中创造更多的就业、价值和知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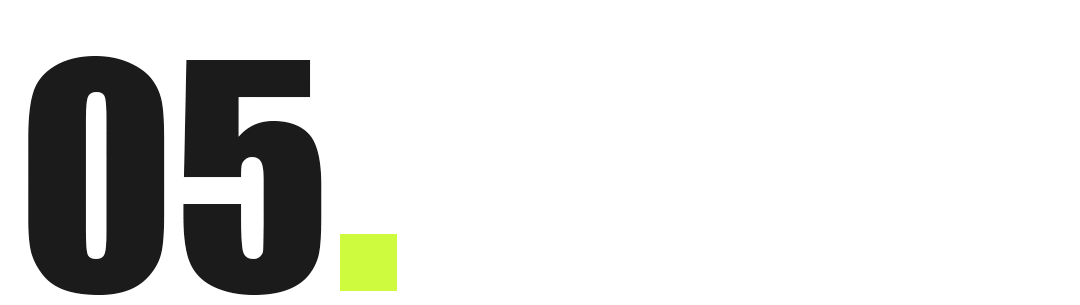
被疫情困在北京一年后,我在离家车程一小时的村子里租了个平房,虽然最初只是个土砖毛坯房,但窗户面对一片小树林,且村子极安静,忽远忽近得只有鸟儿、青蛙、蛐蛐和狗的声音。这是二环里难以想象的。与城市生活相比,村子里的一天总是莫名很长很长,时间仿佛更「经用」了。后来我发现,城市里早上一头扎进办公室,天黑才出来,外面天冷天热刮风下雨都不知道,一天只有一个转场。而村子里从早到晚光线、温度、天色都在变化,一天好像有很多层次的镜头递进。后来比较频繁的户外徒步。春夏秋冬都出了几次门以后,发现了更丰富的流动。比如一座山在冬季是冷峻严肃的,但初夏时就变成明亮的翠绿,秋天则是温柔又丰盛的明黄色。比如一片普普通通的草甸,有一天忽然绽放了无数雏菊和风毛菊,人走过就带起一片纷飞的蝴蝶;比如路边一棵树,春天发芽,夏天开花,秋天路过发现挂了一大捧一大捧橘色浆果,才知道原来是棵沙棘呀。我喜欢爬升至山脊后,延山峦曼妙的腰窝曲线长时间行走。如果能够扎帐就不着急赶路,可以等红日西垂、霞光漫天、山风吹拂,直至皓月当空。我想人只要步入山林,就很难忽略自然的自由、美丽、富饶,因为它们是如此强烈并富有感染力;也很难忽略人类对自然的依赖——来自土壤、河水、降雨、日照,土里的蚯蚓,树木的枝条,蜜蜂的回旋。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地球生病,那么哪怕从最肤浅的层面,生活会变得多么无聊。饮食、娱乐、工作乃至价值观会变得多么令人无法忍受得单调。我不愿想象那种所有消遣只能以买卖为基础的无聊——吃包装好的食品、看剪辑好的内容、去「最出片」的地方打卡。如果没有自然,我们真的就只有商品社会和政治让我们消费的东西了。每一次消费都深思熟虑,是有必要的吗?——但是,为什么不呢。「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(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)」。如果消费是我们生活中最经常做的选择,那它就实际塑造了生活的价值取向,钱包已比口号早一步为我们想要的世界投票。从这种意义上,像Patagonia这样将企业目标「昭告天下」、让自己被消费者反复审视的公司还是太少了。如果有更多的企业在「负责任消费」的赛道上「卷起来」,那么打工人在可支配收入和价值选择之间的矛盾和压力就能小一些。但是在指望大型商业机器转动之时,不妨先给自己安排一趟林间漫步,或者带上环保布袋去农贸市场买瓜果蔬菜,又或者只是上班路上走慢一点,辨别早八点树梢上不同鸟儿的啼声(是的,树上不止有麻雀)。相信会发现山林到底不远人,总是可以为它做一点小事。